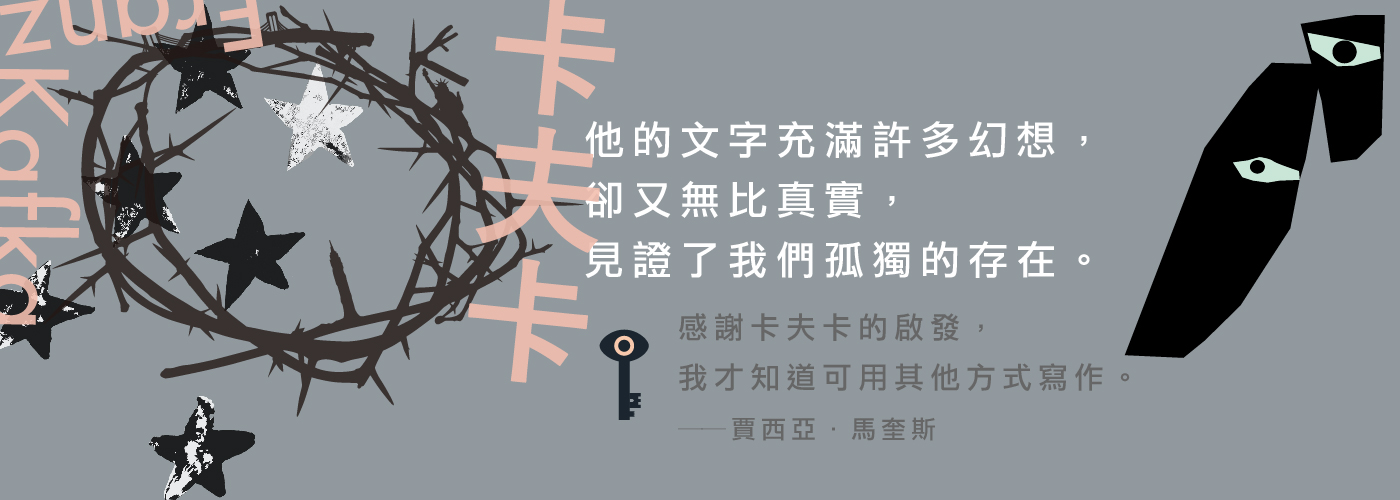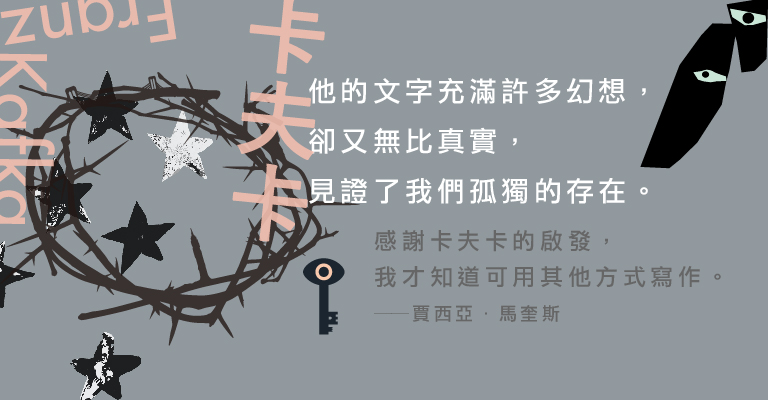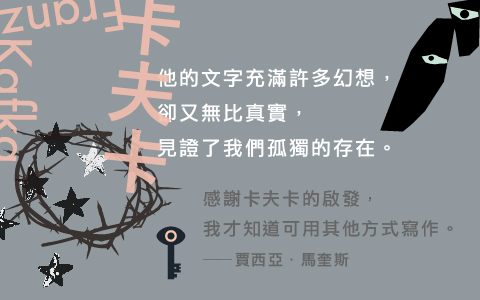「如果你讀了卡夫卡的《蛻變》後,並不認為它只是昆蟲學上的奇想,那麼我就要向你祝賀,你已經加入了優秀而偉大的讀者行列。」
──納布可夫(V. Nabokov)
正是這本小說……將揭示理解卡夫卡的新途徑。
他(卡夫卡)懷著無盡的歡喜寫作此書……這部小說的氣氛比起他的任何其他作品都更樂觀、更「輕盈」,這一點卡夫卡相當清楚。
──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
在他(卡夫卡)生前,只有少數摯友及行家了解他的偉大,了解這個謎樣的非凡人物。只有少數被揀選之人,明白他的短篇散文和三部未完成之長篇小說在哲 學及藝術上的重要性,那三部小說分別是《城堡》、《審判》和《美國》(即《失蹤者》),構成了小說家兼評論家馬克斯.布羅德口中莊嚴的「孤獨三部曲」。
──克勞斯.曼(Klaus Mann)
這是命運,而或許此作品(《審判》)的偉大在於它提供了一切可能,卻未證實什麼。
──卡繆(Albert Camus)
那些把卡夫卡作品當作宗教寓言來讀的批評家則解釋說,《城堡》的K試圖獲得天國的恩寵,而《審判》的約瑟夫.K經受著上帝嚴厲而神秘的法庭的審 判……我們的任務不是在藝術作品中去發現最大量的內容,也不是從已清楚明瞭的作品中榨取更多內容。我們的任務是削弱內容,從而看到作品本身。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我們無法比卡夫卡的《審判》寫得更深入了;他為一個極無詩意的世界創造了極有詩意的意象。──米蘭昆德拉
《審判》是卡夫卡最偉大的作品。
──布羅德(Max Brod)
《審判》最高的藝術成就是,卡夫卡為這些人類語言無法捉摸、無法敘述的事物找到了適當的表達形式、某種物質上的替代品,並且在裡面打造出這些事物的結構,甚至連最微小的地方都鉅細靡遺。
──布魯諾.舒茲(Bruno Schulz)
卡夫卡的作品是如此偉大,它具有某種普世價值。我會很直接將他理解為他是歐洲文化的核心。但在同一時間,我們也分享著他的作品。我十五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他的作品《城堡》,當時我並不覺得「這本書是歐洲文化的核心」,我只是覺得「這是我的書,這本書是寫給我的」。
──村上春樹
如果說喬伊斯的《尤里西斯》是現代版的《奧德賽》,那麼卡夫卡的《城堡》便是現代版的《伊里亞德》了。史詩的世界現在已經無法進入,於是只能從它的反面呈現奧德賽和伊里亞德。
卡夫卡藉著他在官僚世界裡瞥見的幻想,他做成了在他之前看似不可思議的事情:他將某種反詩意至極的素材(極度官僚化的社會的素材)變成小說偉大的詩篇;他將一則極為平庸的故事(有個男人無法得到原先被承諾的職位,也就是《城堡》)變成神話,變成史詩,變成前所未見的美。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城堡》徹頭徹尾是部自傳性小說。原本應該以第一人稱述說的主角被稱為K;他就是作者,太過確切地承受了所有這些痛苦、這些怪誕的失望。
──托瑪斯.曼(Thomas Mann)
卡夫卡將社會結構視為命運,不僅在《審判》和《城堡》中,卡夫卡在龐大的官僚等級制中面對命運,而且在更具體的、艱困的無法估量的建築工程中也瞥見命運。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猶太人」這個詞在《城堡》中沒有出現。但顯而易見,卡夫卡從他的猶太心靈出發,通過這麼一個樸素的小說就今日猶太民族的整體處境所說的話超過了一百篇學術論文可以告訴我們的內容。
──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
每個天才的作家在寫作時他的心理上都是殘疾的,比如福克納、海明威、卡夫卡……當你不得不思考生命、生存的問題時,《城堡》值得一看。
──閻連科
城堡似乎是一種虛無,一個抽象的所在,一個幻影,誰也說不清它是什麼。奇怪的是它確確實實地存在著,並且主宰著村子裡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裡的每一個人身上體現出它那純粹的、不可逆轉的意志。K對自己的一切都是懷疑的、沒有把握的,唯獨對城堡的信念是堅定不移的。
──殘雪
綜合評論
如果要舉出一位生於我們這時代的作家,卻可以和但丁、莎士比亞和歌德相媲美,那麼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應該是卡夫卡。
卡夫卡對我們至關重要,因爲他的困境就是現代人的困境。
──西蒙.波娃(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
要充分欣賞卡夫卡作品的純粹與其特有的美時,有一個絕不能忽略的觀點:這是一個失敗者的純粹與美麗。
至於大城市居民的體驗,我有許多想法,首先,我想到的是現代市民清楚自己是聽由一架巨大的官僚機器擺布著,這架機器由權威操控著,而這權威即使對於那些它們要對付的人來說就更模糊不清了。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卡夫卡在二十世紀作家中居於首位。
我寫故事,是抱著極大的野心成為卡夫卡去寫,但成效甚微。其中一篇名為〈巴別塔圖書館〉,還有其它篇章,那些都是我試圖成為卡夫卡的習作。
最初我認為卡夫卡是文壇前所未有、獨一無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後,我覺得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的文學作品中辨出了他的聲音,或者說,他的習慣。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卡夫卡是一個先知式的作家。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卡夫卡同他的上帝爭執道德上的偉大、啟示、善與一致性——但只是為了更熱切地投入他的懷抱。荒誕被認識了並被承認了,人只有聽其自然,我們從這一剎那知道,它不再是荒誕了。
「卡夫卡的完整藝術」是迫使讀者一再地以不同觀點去閱讀其作品。
──卡繆(Albert Camus)
我知道真正的寓言只有《聖經》裡的。我也看過一些其他的,像紀伯倫……可是你不會在裡面發現《聖經》才有的那種靈魂。現在只有卡夫卡的作品,還算有些接近。
──巴布.狄倫(Bob Dylan)
我無法閱讀其作品的反常,人類的心智還不夠複雜到足以閱讀他。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很多人形容我的劇本是捷克版的荒謬劇。我個人是沒有資格去評斷,荒謬劇做為一種藝術潮流,我到底從中學到多少或被引導到什麼程度(或許有那麼一些,但我認為卡夫卡的影響更強)。
──哈維爾(Václav Havel)
不是孤獨的詛咒,而是被侵犯的孤獨,這才是卡夫卡揮之不去的執念。
我如此熱切地執著於卡夫卡的傳承,有如捍衛我個人遺產那般捍衛他,這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模仿那無從模仿的事物有什麼用處(然後再一次發現卡夫卡式的東 西);而是因為卡夫卡的傳承,是小說(是作為小說而存在的詩)徹底自主性非常了不起的例子。憑藉這樣的徹底自主性,卡夫卡對於我們的人類境況(一如它在我 們這個世紀所展露的)說出了社會學或政治學反思所無法告訴我們的事。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精心設計、充滿好奇的縝密、客觀、清晰透明、適切的文體形式,一個準確寫作的保守主義者。
──托瑪斯.曼(Thomas Mann)
感謝卡夫卡的啟發,我才知道可用其他方式寫作。
──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和卡夫卡比起來,詩人里爾克、小說家托瑪斯.曼都相形見絀、毫無生趣。
──納布可夫(V. Nabokov)
卡夫卡深深根植於人類生活的悲劇之中,他那無比清晰的作品,足以描摹出人類徹底破碎的形象。較之於僅僅停滯在心理意義的普魯斯特,或總是試圖用神話術語和語言魔力進行創作的喬伊斯,卡夫卡的探索無疑又前進了一步。正因為極度的痛苦吞噬了他,這是一種形而上的痛苦,卡夫卡才成為了與虛無抗爭的現代人的最忠實的、悲劇性的見證者。
──丹尼爾.羅普斯(Daniel Rops)
卡夫卡的世界充滿許多幻想,卻又無比真實。
正因為卡夫卡的證詞是如此深刻地獨特,所以就更加普遍。
──沙特(Jean-Paul Sartre)
作家沒辦法想他們想寫,他們只能寫他們能寫。當我二十一歲的時候,我想寫得像卡夫卡。但不幸的是,我卻寫得像是《辛普森家庭》的編審寫的。
──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
卡夫卡即使在現代所未具有的、最錯置的詞組中,仍擁有現實的魔力。令人牙齒打顫、隱隱作痛。
卡夫卡是「嚴肅文學」中最後一個說故事者,除了模仿他,沒有人知道要往何處去。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哪個作家比卡夫卡更孤獨,但也只有很少數的人,才能達到他所引發的共鳴。」「卡夫卡並沒有救我,他只是告訴我,我正在往下沉。」
「世界上荒謬劇的模式只有兩種,一種是一直在等待著什麼,另外一種是早上起來變成了甚麼。如果你們除此以外,還能想到別的,將會留名青史。」
——平田織佐(當代日本劇場導演與編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