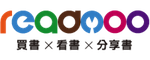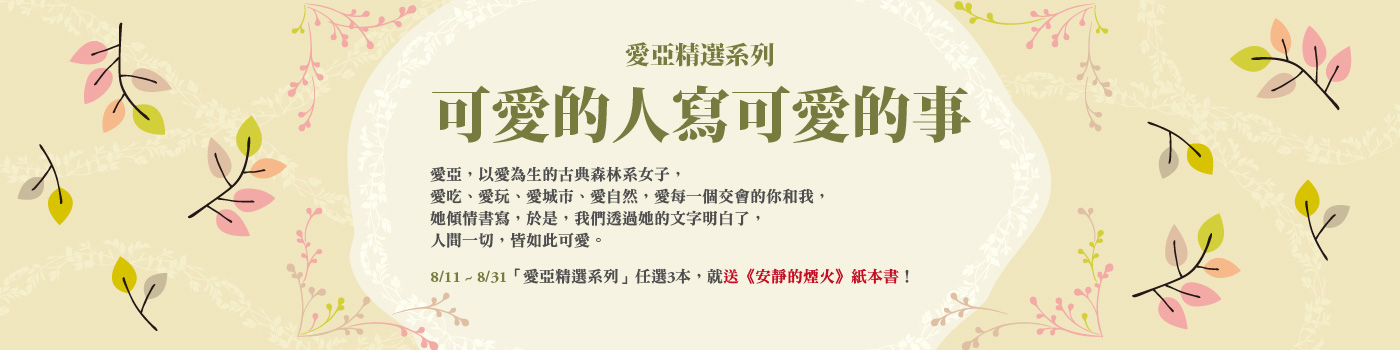少女、俠女、有情女——我所認識的愛亞姊姊
有時星星亮起,依然是當年少女
我們約在北京五道營胡同靠近雍和宮的入口處碰面,愛亞姊一身棉布衣裙飄然而至。遠遠的,我望見她一臉的恬然,短髮瀏海往側邊別了一枝小巧的髮夾,掉落的幾根髮絲隨風擺動。
我走向前去迎她,她立即綻開一大朵笑容,伸出雙手執住我的手。 「前頭這一家咖啡館好嗎?」我問。 「都好,只要跟你說說話,哪一家都好。」她答,聲音依舊甜嫩如故。
這是我第一次做為「朋友」、做為「地主」,和愛亞姊單獨約會。那是二○一○年,四年前的夏天,我離開台灣,在北京主持一家兩岸三地合資的文化公司,草創初期,千頭萬緒,一聽說有台灣故人來訪,而且是多次出版界聚會遇見但多半僅止簡短寒暄的文壇大前輩愛亞姊,想起她好聽的嗓音,心生強大的歡喜,開開心心地赴約了。
當我告訴愛亞姊,其實我們認識已經近二十年了時,她詫異地偏著頭望著我,似乎索盡枯腸仍一無線索而茫茫然。
遙遠的一九九二年,我與幾個友人,組了一家小小的專門出版青少年文學的出版社,第一年的第二本書就有幸拿到了該年中國時報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獎,獲獎後受邀談書的第一個廣播節目便是中廣的「愛亞與青少年」。當時我多麼緊張啊,不僅因為是第一次對著麥克風說話,更因為當年愛亞這個名號已經是小文青如我心目中的「超級大咖」,畢竟,她先後獲得金鼎獎的散文集《喜歡》,以及獲得中興文藝獎章的小說集《愛亞極短篇》,是文青們的愛讀作品與討論話題,而愛亞也成了後來風靡多年的極短篇創作與閱讀熱潮的重鎮。
我便是懷著如此忐忑不安的心,結結巴巴地獻出廣播錄音的初體驗。在那彷彿乘坐火車始終到不了站的漫長時間裡,愛亞姊一直平和地、輕柔地說「慢慢來,別緊張……」,那甜甜的、嫩嫩的如少女般,卻又有著高度安定人心力量的嗓音,在我心中留下了無法抹滅的印象。而我也在那嗓音與面容裡瞧見了一縷深深的哀愁。
那之後,我到書架上重新翻出她在爾雅與張曉風、席慕蓉合著的《三弦》(一九八三),讀到蔣勳先生在序裡談中國文學與愛亞:
「沈從文像《詩經》,他的人是歲月中的人,生死榮枯只是時序,所以不憂。 我寧願要朱自清的平時。平時至少是不做態,即使生活再平凡,也不落到為散文而散文,才會有〈背影〉這樣的文章。 文章本是此身,離開此身並無文章。 愛亞則最為平直,沒有詞藻的修飾,小說回復成了故事,另有一種趣味。」
我不禁頻頻點頭,我讀的愛亞與我所見的愛亞並無二致。但那哀愁又為何?
心是熱的,回眸凝望所有的曾經
查了相關報導,才知愛亞筆名的由來,她深愛的另一半周亞民先生因為肝病於一九九○年春末不幸離世了。「啊,還這麼年輕,才不到六十歲哪。」我仿如能觸到前日所見那面容背後的那縷哀傷,於是,又翻開《十二樓憑窗情事》(一九九一),讀到愛亞寫給《百年孤寂》裡的美美(莉娜塔.瑞米迪歐.邦狄亞)的信:
「一如你頭頂經常出現並停留旋飛的那些美麗黃蝴蝶,妳與妳的愛情迷惑了我。妳唯一的反抗只是不說話而已——以後終生不再說話。
妳竟然如此消極!棄他於不顧,只以啞口作為抗議。每每思及妳與巴比隆尼亞一個心死一個身殘,各自一方孤寂數十年,折磨數十年,我便忍不住皺眉,甚至打起寒顫來,那種恐怖的寒顫!……妳本性中的叛逆、大膽、瘋狂尚不足夠麼?……妳的選擇卻是在修道院中無言的度日、老去、死亡。沒有癡,沒有瘋。對不起,我不可理喻到寧可妳是癡的、瘋的!」
「對不起,我不可理喻到寧可妳是癡的、瘋的!」我口裡跟著這封信喃喃地念著。忽然,我明白了愛亞的悲傷,那是一種癡傻的、瘋狂的熱愛。
不僅愛人、她愛生活、愛世界一切,包括樹、花、小貓小狗、小溪小房子,還有山上的石頭,但常常生氣,氣人們不夠愛、不夠奉獻、不夠付出,只是氣,只是無奈,而沒有憎、沒有恨,於是寫文章自剖、傾訴、叨念、提醒,也抱不平。
如同她在散文集《喜歡》的後記裡的自述:
「初初開始寫的是小說,在常年繁亂冗雜的工作與生活中,一直將寫小說當作一項發洩,一項快樂,一項自己與自己共處時的祕密。……小說可以是假設的,可以移情的,可以補償的,可以忘我的,而散文卻是心中始終不敢碰觸的一柄尖利的刀子!那是要褪盡衣衫,將皮肌整個兒袒露向人的一種裸啊!最最真實無處可隱可遁的裸!」
平直、真實、袒露、沒有任何矯飾,我理解到,這就是愛亞的癡傻。
十五部經典電子書上線,如安靜的煙火,盛大綻放
北京一見後,幾經周折,二○一二年返台述職的我再次見到愛亞姊的契機,則是與作家張耀升的會面。他提起愛亞姊正在進行的「台灣花與樹」的寫作計劃,問我是否有興趣出版?我當然欣喜有加,之後,在群傳媒執行長暨群星文化發行人龐文真女士的大力支持下,致電聯繫愛亞姊。當手捧著一疊厚厚的書稿細細閱讀,心中感受到的溫度一如既往,如春暖陽。
「而她是熱情的鳳凰花。……那是丈夫病著公司撐著三個孩子都在念書的人生路段,我靠著眾多如她一般的朋友這樣幫忙那樣幫忙平安度過。而一再助我一直站在我身旁的她卻再也不見。……熱情愛我的鳳凰花,你在哪裡?你好嗎?」
這疊稿子後來整編為今年二月出版的《安靜的煙火——我的臺灣花.樹》(群星文化),以電子書先行、紙本書在後,幾乎同步出版的形式,在國際書展堂堂亮相,吸引了眾多等候愛亞新書問世多時的書迷同賀。
在準備推出《安靜的煙火》同時,群星文化也開始積極籌備愛亞經典系列十五本電子書的重新整編、上架,安排在今年暑假隆重推出,讓更多新世代的讀者認識她,靠近她 。
我一邊重讀著這些歷久彌新的文章,有小說、散文、寫給青少年的成長系列,一邊回想著我與愛亞姊之間長期而淡如清水的交誼,不禁要深深地感佩起這位永遠與文學、與寫作、與天地、與有情萬物熱烈繾綣的奇女子了。這般平凡但不流俗如《脫走女子》、這般夢幻奇思如《是誰在天空飛?》、這般柔柔切切地跟你《握手》,這般懷有點燃自身與他人心中熱力的大能量,始終是她。
是愛亞。